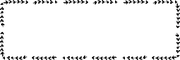当柴静直面杨永信,问他怎么治疗孩子的时候。杨永信微笑着说。
“就是电击。”
“就是借助电休克治疗仪。”
“一边电他一边问他为什么要来这啊,还敢不敢啦。如果他回答错了就继续电。一直到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为止。”
说这些话时杨永信一直是笑着的,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,仿佛在炫耀着自己的功绩一样。好像确实也是他的功绩。
杨永信,山东省临沂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,被称为“全国戒网瘾专家”,以使用电击方式治疗网瘾少年而闻名。“杨永信”之所以存在,得‘益’于有一群忧心忡忡的家长——他们时刻担心着,“这一代的孩子”会被恐怖的网瘾毁掉。
如果将视野继续扩大,我们则会发现不独中国的家长如此,世界各地的“过来人”们都对下一代的孩子们忧心忡忡。在他们眼里,“这一代的孩子”意志薄弱、没有上一辈的坚强精神,沉迷于虚幻的网络,恐怕要成为“毁掉的一代”。
本文聚焦于“过来人”的一个重要忧虑——现在的孩子广泛的使用电子产品,他们的社交能力都要被毁了。通过本文,我们得到两个问题的答案:(1)Are Children’s Social skills declining? 一代不如一代了吗?(2)Does screen exposure diminishes children’s ability? “手机”毁了这一代吗?
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孩子的社交能力(social skills),作者使用教师(及家长)对孩子人际交往能力、自我控制能力的评价进行度量。上图中,长线代表教师对孩子社交能力的评价,短线代表家长对孩子社交能力的评价;实线代表“这一代孩子”的社交能力,虚线代表“上一代孩子”的社交能力。上图的描述统计信息以及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——
无证据显示,儿童的社交技能下降了(一代不如一代)。
我们得到了问题1的答案,但问题1的答案无法回应问题2。“这一代孩子”社交技能没有下降,原因可能在于这一代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更加重视了、家庭条件改善等等,屏幕使用仍可能对社交技能存在负向影响。因此,作者仍将继续考察屏幕使用对社交技能的影响。但对因果识别的一个挑战就是,社交能力差的孩子可能更喜欢玩手机(电脑等)。作者以孩子五年级时的社交能力为被解释变量,但在分析中控制孩子幼儿园时期的社交能力,这一操作能够降低各类未观测因素的不利影响。
上面的表格呈现了回归结果,作者在同队列数据内使用“逐步回归”法进行分析。首先,仅考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,不加入各类控制变量;紧接着,逐步的加入父母培养(反映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及参与程度)变量、SES(社会经济)变量、先验社交技能(幼儿园时期社交技能)变量。虽然第一列回归结果显示,屏幕使用变量对孩子社交技能存在或正或负的显著影响;但当控制变量逐步加入后,这些显著作用均消失。这表明,屏幕使用和社交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,但无法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其他队列分析及大量的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这一结论。因此——
无证据显示,屏幕使用会降低孩子的社交技能。
至此,问题1和问题2的答案我们都已经获得。一代不如一代吗?没有证据!手机毁了这一代吗?没有证据!实证分析结果无法支撑社会大众尤其是家长们的忧虑。那么,为什么从美国到中国,“过来人”们都如此忧心“这一代孩子”?
当电影出现后,“过来人”在疾呼:电影要毁了这一代孩子!
当电视出现后,“过来人”在疾呼:电视要毁了这一代孩子!
当电子游戏出现后,“过来人”在疾呼:游戏要毁了这一代孩子!
当手机出现后,“过来人”在疾呼:手机要毁了这一代孩子!
现在的“过来人”仍在大声疾呼:微信要毁了这一代孩子!抖音要毁了这一代孩子!**/肖战要毁了这一代孩子!
每当新的技术、新的产品、新的社会流行出现后,“过来人”们感到陌生。“这一代孩子”的生长环境和“过来人”完全不同,这种陌生会转化为焦虑甚至恐惧:我们“过来人”饱经风霜、饱受磨难、意志坚定…难道“这一代孩子”要在电脑/手机/抖音…中迷失自我而毁掉吗?强烈的不安与强烈的责任感(对孩子的责任感、对社会的责任感、对人类未来的责任感)驱使着“过来人”们大声疾呼。但是,当技术、产品或流行变的普遍之后,之前的种种焦虑完全消失,回望之后这些焦虑甚至显得滑稽。
本文作者坦诚,研究具有很多局限(例如,教师评价/家长评价能否捕捉社交能力变化;屏幕使用负面作用可能体现在其他年龄段而非幼儿园到五年级等等),但本文是首次使用代表性数据对考察这一热点社会议题的实证研究,而实证研究的数据质量、变量测度、因果验证等各个环节都会随着后续研究的推进而不断改进。面对本文的研究结论,我们是应警醒的是——
相比于“手机”,或许部分家长和“杨永信”更能毁掉“这一代孩子”。